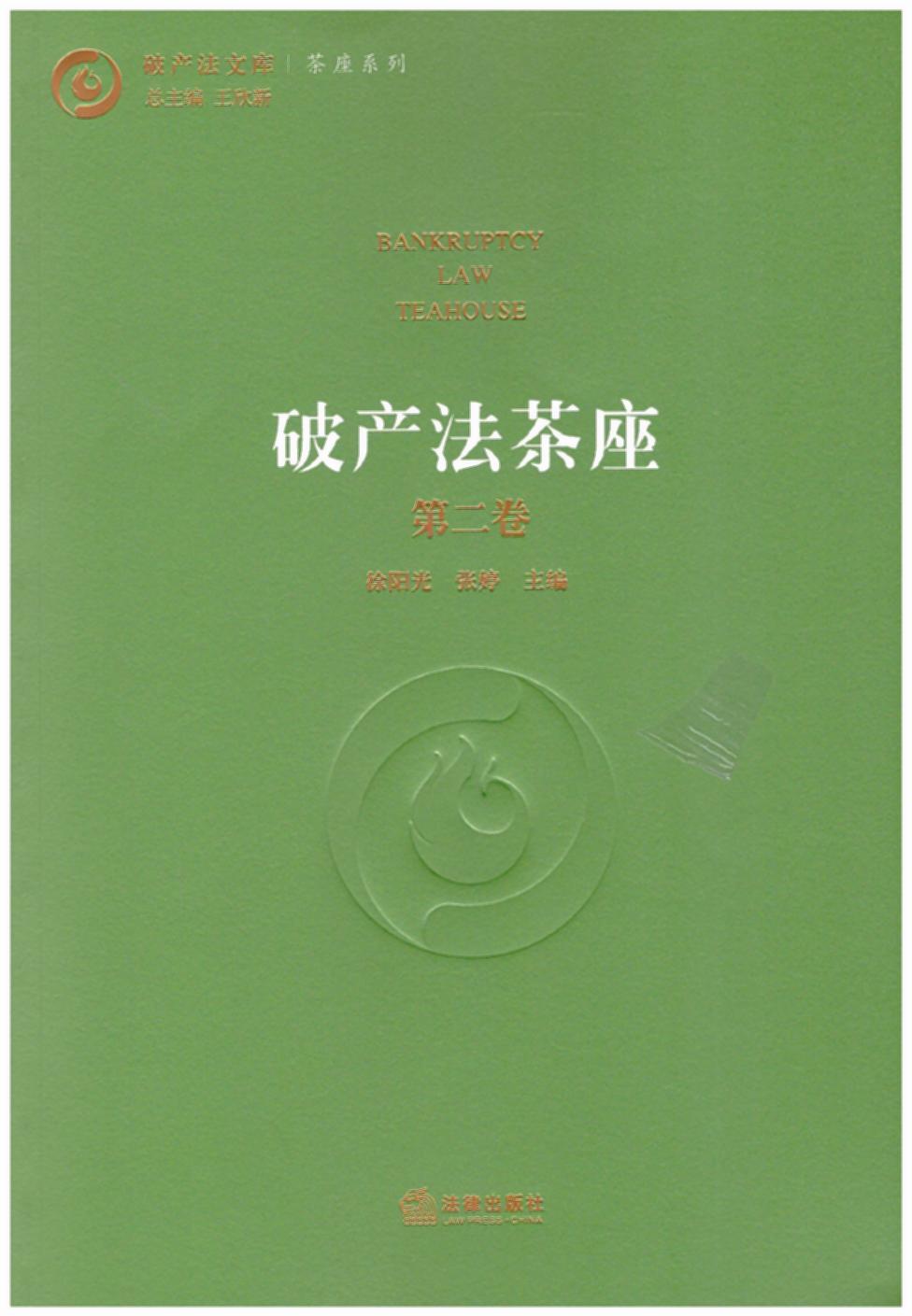
“三鹿”破产的法学困惑及大规模侵权破产的样本意义
韩长印
三鹿集团破产案件已经过去很多年了,但笔者仍有挥之不去的法学困惑以及对于同类案件可能重演的顾虑。
据《广州日报》2009年11月29日第A2版报道:“备受关注的三鹿奶粉赔偿事件被画上句号,结石患儿将无法从三鹿获得任何赔偿。”“记者昨天上午获悉,石家庄中院日前作出裁定,终结已无财产可分配的三鹿破产程序。裁定中显示,三鹿对普通债权的清偿率为零。这意味着,结石患儿将无法从三鹿获得任何赔偿。”
一、隐含在“三鹿”破产中的法律困惑
(一)个别优先赔偿的做法合乎情理却不合法
据报道,三鹿集团等22家责任企业在“三鹿”破产之际先行向乳制品业协会支付9亿元作为受害者的现金赔付,另拨出2亿元设立赔偿基金,这些做法虽然获得了政府和社会公众在心理上的普遍认可,但与《企业破产法》关于破产财产的处理方式和分配顺序的规定是不相一致的。按照《企业破产法》第113条第1款的规定,破产财产清偿顺序是:“(一)破产人所欠职工的工资和医疗、伤残补助、抚恤费用,所欠的应当划人职工个人账户的基本养老保险、基本医疗保险费用,以及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应当支付给职工的补偿金;(二)破产人欠缴的除前项规定以外的社会保险费用和破产人所欠税款;(三)普通破产债权。”而因为产品质量问题造成的损害,受害人所应获得的赔偿,按照我国现行相关民商法的规定,应当一律列在上述清偿顺位中的第三顺位。
(二)破产法关于董事、高管民事责任的规定形同虚设
《企业破产法》第125条第1款规定:“企业董事、监事或者高级管理人员违反忠实义务、勤勉义务,致使所在企业破产的,依法承担民事责任。”对照该款规定,三鹿集团的董事、高管在明知在牛奶中添加三聚氰胺会对消费者的生命权、健康权造成危害的情况下,仍然指令公司继续生产,其对受害人构成一般民商法上的侵权以及破产法上对债权人忠实义务和勤勉义务的违反的事实至为明显,但我们并未看到该案追究董事、高官民事责任的相关报道。这致使上述《企业破产法》的规定成为一纸空文。
(三)政府垫付费用的放弃追偿可能助长大规模侵权行为的政府埋单
据报道,“三鹿牌婴幼儿奶粉事件发生后,党中央、国务院对此高度重视,在第一时间对严肃处理三鹿牌婴幼儿奶粉事件做出一系列部署,立即启动国家重大食品安全事故一级响应,对患病婴幼儿实行免费救治,所需治疗费用由同级财政预拨垫支,中央财政对确有困难的予以适当支持。这一系列措施对稳定社会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的确,以国家的公共财政对重大食品安全问题垫付相关救治费用本身无可厚非,这也是各级政府的职责所在。但问题的关键在于,如果这些费用垫付之后不向相关责任主体(该案中由于企业已经无产可破,应当指向相关直接责任人员)追偿,不能最终转由侵权企业及其直接责任人承担,这不啻为“企业侵权行为风险的外部化”的负面案例,而企业违法行为风险承担的外部化最终会助长侵权行为愈演愈烈。
二、“三鹿”受害人获优先赔偿的社会
认同及现行立法的逻辑矛盾
我们注意到,对于三鹿集团在濒临破产之前向中国乳制品业协会优先垫付医疗费用、死亡或者伤残赔偿款的做法,社会公众在“三鹿”破产案件的处理过程中并没有提出任何异议。可见,对生命权、健康权受到侵害的受害人的优先受偿问题,社会公众在伦理层面是普遍给予认同的。
实际上,《企业破产法》第113条第1款规定了两个序列的一般优先权:(1)破产人所欠职工的工资和医疗、伤残补助、抚恤费用,所欠的应当划入职工个人账户的基本养老保险、基本医疗保险费用,以及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应当支付给职工的补偿金;(2)破产人欠缴的除前项规定以外的社会保险费用和破产人所欠税款。
从上述第一顺位优先权的内容来看,其中“医疗、伤残补助、抚恤费用”“应当划入职工个人账户的基本养老保险、基本医疗保险费用”以及“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应当支付给职工的补偿金”,均属于保障人身健康和获得医疗条件的必需费用。这些费用的性质和用途绝大部分与生命、健康或者身体遭受“三聚氰胺”之害通常所计算赔偿的项目、内容、性质和用途相吻合。从这个角度上讲,无论这些费用是发生在破产企业的员工身上,还是发生在社会公众身上,都应当予以优先赔偿,如果这些费用不予赔偿或者不能给予足额赔偿,将直接影响受害人的生存和健康。
问题在于,《企业破产法》将破产企业所欠企业职工的上述债权列入优先权范畴,而对于企业之外作为社会一般人的人身损害赔偿之债的上述费用和请求权列入普通债权,而按比例进行分配,其逻辑上的问题在于:同样的债权性质、赔偿责任类别和用途,仅仅因为债权人的身份不同,即一类系破产企业职工,另一类系破产企业职工以外的社会一般受害人,就“内外有别”地排列为高低不同的分配顺位,这显然有违设立这项优先权制度的初衷,未必能够完全实现设立该项制度所追求的最终社会政策目标。毕竟,优先权在这个问题上的排序,不应当根据权利人的内外身份,而应当依照权利的性质(满足基本生存需要和医疗等需要的最低社会保障性质)确定是否统一赋予其优先权顺位。
三、“三鹿”作为大规模侵权破产的样本意义
现代工业的发展,在环境污染、产品(食品、药品)质量、安全生产等方面都催生了许多大规模侵权事件。该类事件往往因受害人数众多、时间跨度较长、赔偿金额巨大而极易导致侵权债务人破产。在侵权债务人破产之时,现行破产法所确立的担保债权优先受偿、侵权之债和普通合约债权平等受偿的规则,往往使人身损害的受害人得不到必要的救济,并且无益于实现侵权责任法遏制侵权行为之基本功能。
在我国,大规模侵权事件并不鲜见,甚至呈层出不穷之势,比如安徽省阜阳市劣质奶粉致本地及其他地区婴幼儿因营养严重缺乏而大量伤亡事件(又称“大头娃娃事件”)、中国东部滨海经济带由于环境污染而产生的“癌症村”现象,以及中国石油股份有限公司吉林石化公司爆炸事故导致的松花江重大水污染事件。为社会所广泛关注的三鹿集团“三聚氰胺毒奶粉”事件则属更为典型的一例,只是说,“三鹿”破产把相关问题推到了社会焦点的浪尖之上。
更为严重的是,如果没有物权法上的穷尽破产债务人所有可担保财产的“浮动抵押”和“应收款质押”等制度存在,那么,企业破产时或许会给普通债权留下或多或少的责任财产(包括划人职工个人账户之外的社会保险费用)而当物权法穷尽了担保债务人可以用作担保的一切财产,而不给普通债权预留哪怕是满足侵权之债的受害人基本生活和医疗等费用的责任财产时,立法对普通债权,尤其是人身侵权之债的普通债权的“人道救济”问题,就会凸显。
本来,侵权行为法的立法目的有三:对受害人予以赔偿、对侵权行为人予以惩罚、预防侵权行为的再次发生。但当实施侵权行为的企业陷入破产之时,侵权行为法的预防和惩罚功能基于侵权人的不复存在而失去原本的预防和惩罚意义,或者仅仅具有“画饼充饥”的作用,对于受害人来讲,补偿的作用则可能凸显为唯一可以期待的目的。
民商法理论研究表明,人身侵权之债除了侵权行为人的赔偿之外,还有社会保障制度和商业保险制度等多元的救济渠道,甚至未来侵权法发展以及与此相关的赔偿补偿体系的未来框架,主要应由侵权行为法、无过失补偿制度、社会安全体系三者构成一个相对完善的补偿体系,然后逐步从以侵权行为法 。担负分配损害的主要机能的倒金字塔形转向平方型(平衡型),即三方比重呈平衡状态,最后渐次移向金字塔形。
但不可否认的事实是,我国社会当下的社会保障水平只是处在一个“金字塔”的“塔尖”位置,其能够发挥的救济作用非常有限。故而,在社会救济之外寻求不同利害关系人之间对风险的重新分配方案,仍然是我们万般无奈而又必须作出的选择。
在当下的破产实务和强制执行案件中,相关司法解释已经注意并对该问题作出了不同的处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二)》第16条规定,债务人对债权人进行的以下个别清偿,管理人依据《企业破产法》第32条的规定请求撤销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1)债务人为维系基本生产需要而支付水费、电费等的;(2)债务人支付劳动报酬、人身损害赔偿金的;(3)使债务人财产受益的其他个别清偿。又如,《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刑事裁判涉财产部分执行的若干规定》第13条规定:“被执行人在执行中同时承担刑事责任、民事责任,其财产不足以支付的,按照下列顺序执行:(一)人身损害赔偿中的医疗费用;(二)退赔被害人的损失;(三)其他民事债务;(四)罚金;(五)没收财产。债权人对执行标的依法享有优先受偿权,其主张优先受偿人民法院应当在前款第(一)项规定的医疗费用受偿后,予以支持。”但相关规定是否对所有的破产案件均具有普适意 义,仍有进一步思考的空间。
总之,如何重新审视并理顺担保物权、侵权之债、普通合约债权等不同性质的债权在破产清算程序中的地位及其应有的和谐关系,是大规模侵权致使侵权企业破产之时破产法所面临的新课题。
摘自:《 破产法茶座(第二卷)》,法律出版社2017年9月出版。
微店链接:https://weidian.com/item.html?itemID=2188426605
淘宝链接: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id=56076099961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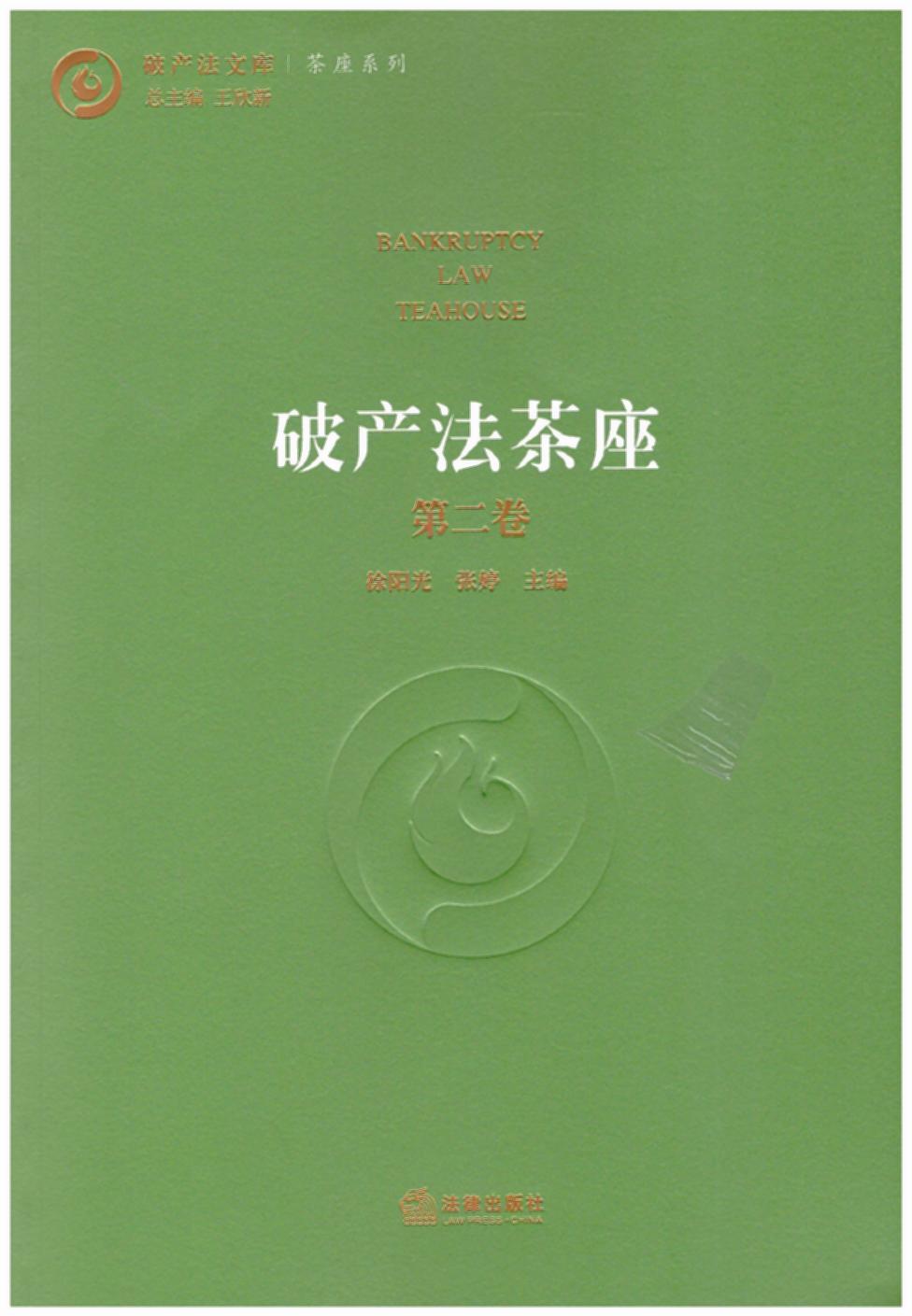 “三鹿”破产的法学困惑及大规模侵权破产的样本意义
“三鹿”破产的法学困惑及大规模侵权破产的样本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