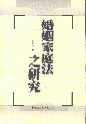
《婚姻家庭法之研究》:
通奸与精神上之损害贻偿
第一节 序 说
1.于今日,通奸行为是夫妻间守贞义务之违反,但在末开化社会里,无所谓守贞义务之观念。依缪勒利尔(F.Muller-Lyer)之所言,澳洲土人以其妻为物品而严加看管,非得他的承认或允许,不得乱用或夺去,因此,其惩罚妻之通奸行为,不是由于两性的嫉妒,而是因为所有权被人侵犯。所以末开化民族之原始人,常常惩罚违反其意志之通好,但却愿意以妻招待客人,任其通奸。由此可知,贞操之漠视,是未开化民族两性生活的一种特征。一般而言,进入文明时代后,守贞义务的观念才渐渐被建立起来,但对于夫妻守贞义务之要求程度,却有差别。在我国古代,秦之法制关于夫妻守贞义务之要求,较符合男女平等之原则。“防隔内外,禁止淫佚,男女絜诚,夫为寄豭(言夫淫他室,若寄豭之猪),杀
之无罪”(《史记·秦始皇本纪》)。即谓夫亦有守贞之义务,若不守义务,而与他人通奸,其妻可得而杀之。但后律至清律,关于夫妻之守贞义务,却设有不同之标准。妻妾之通奸为有夫奸,系加重奸,夫之通奸乃同凡好,且妻之淫佚为七出之条件之一,男子纳妾被视为理所当然。日本旧民法以妻之通好为离婚原因之一(日本旧民法第813条第2款),刑法亦仅罚妻之通奸(日本旧刑法第183条),对夫则不要求其守贞。诸此规定,皆与男女平等之原则有违。现行法以一夫一妻制为婚姻之基本原则,法律上,不允夫有纳妾之行为。夫与妾之通奸乃纳妾后之必然结果,妻可据以请求离婚(1937年上字第794号、1940年上字第172号、1943年上字第5726号)。
2.在外国立法例上,如法国民法明定夫妻相互负有忠实(fidelite)、扶助(secours)、协力(assitance)之义务(法国民法第212条)。瑞典婚姻法规定夫妻互负诚实及协助之义务,并应为家庭幸福而协力(瑞典婚姻法第五章第1条)。民法并无明定夫妻有守贞之义务。但,依“民法”规定配偶通好为离婚原因之一(“民法”第1052条第1项第1款),且在刑法上有通奸罪之规定(“刑法”第239条),因此学说上都一致认为夫妻互负守贞义务。判例上亦认为夫妻之一方违反此义务而与人通好者,系侵害他方配偶之权利,他方配偶得对其请求精神上之损害赔偿(1966年台上字第2053号)。实务上大多认为配偶之一方与配偶以外之人通奸系侵害他方配偶之权利,故以侵权行为责任论之。但,以前法国之判例认为通好配偶之通奸行为,系婚姻义务之违反,应负债务不履行之责任,而日本学者中川善之助、鸠山秀夫、横田秀雄均采此说,下级审亦有采此说之判决。在实务上如前述1966年台上字第2053号之判例谓:“配偶之一方行为不诚实,破坏共同生活之圆满安全及幸福者,即为违反婚姻契约之义务而侵害他方之权利。”似在说明通好配偶之通好行为系债务不履行。虽然该判例以侵权责任论之,但实质上,似应含有更深一层之意义,此为本文所欲究明之点之一。
3.又通奸非一人所能为,因此讨论损害赔偿责任时,不能仅论通奸配偶之责任。关于相好人之责任,学说上、实务上亦多以侵权责任论之。若将相好人之通奸行为解为对被害配偶之侵权行为,则被害配偶因通奸所受侵害之权利,究属何种性质,在学说上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而实务上亦以“至于所侵害者系何权利,则非所问”云云,一语带过,避而不论。因此,关于被害配偶受侵害之权利的性质,亦为本文所欲宪明之点。关于男女因婚姻之成立而互相拥有何种之权利,康德从性的观点提出了极为露骨又非常近代化的婚姻理论。本文将以康德之婚姻理论为基础,来讨论被害配偶因通好所受侵害之权利的性质。
4.关于损害赔偿有财产上之损害赔偿与非财产上之损害赔偿,而非财产上之损害赔偿又可分为回复原状与精神上之损害赔偿(或称慰抚金)。本文所讨论的,仅限于精神上之损害赔偿。惟关于精神上之损害赔偿,依第18条第2项之规定,以法律有特别规定者为限,始可请求。因此在讨论配偶之一方因他方配偶通奸而精神上受有损害之场合,能否请求精神上损害赔偿之问题时,势必要讨论第18条第2项,第184条与第195条之关系,此亦为研究人格权之一大课题。惟此非本文之研究重心所在,仅于结论附带检讨。
第二节 台湾地区之学说
1.一般而言,因他方配偶通好而受有财产上之损害时,得依第184条向相好人请求赔偿,此在学说上或实务上均无异论。但关于精神上损害之赔偿,则有肯定与否定二说。采否定说之学者有谓:“在民法上,除因通好而诉求判决离婚者,得依第1056条第2项之规定,请求赔偿非财产上之损害外,仅因通奸而请求通奸者及相好者给付慰抚金,以赔偿精神上之损害,尚无明文之根据,故不能与法日之学说判例为同一之解释。”从法条之规定来观之,此说之见解并无错误之处,但从民法赔偿被害人损害之精神来观之,则对于被害配偶似有保护不周之嫌。仅注意到法的安定性,而忽略法的具体妥当性,是此说的缺点。亦即局限于有限条文之规定,坚持“恶法亦法”之主张,而不对法条作适当之解释与活用,以致无
法保护被害人之利益,而违背民法之精神。因此,此说恐难赞同。
另一采否定说之学者谓被害配偶在民事上得依第1052条第1项第2款之规定据以请求法院判决离婚。并得依第1056条之规定向对方请求赔偿财产上或非财产上之损害。被害配偶并得依第184条第1项向通好配偶及相好人请求赔偿其财产上之损害。凡此均为法律所明定,用以维护生活之圆满、安全及幸福。法律之保护,已相当周密,木须在法律之外,另予非财产上之损害赔偿。惟被害配偶因通好所受之财产上损害,毕竟不多,诚如王泽鉴教授之所言:“在通常情形,与有配偶者通奸而造成财产上之损害,究属不多,纵或有之,赔偿数额亦甚微小,故若不使受害人请求相当之慰抚金,则加害人几可不负任何责任,非特不足保护被害人,对于公益亦有不利。”此说之不当,由此可知。
2.由于第18条第2项规定人格权受侵害时,以法律有特别规定者为限,得请求损害赔偿或慰抚金。而从第195条规定之形式来观之,似又仅限于身体、健康、名誉或自由被不法侵害时,始可请求精神上之损害赔偿。因此,为了保护被害配偶之利益,而产生种种学说,从不同的角度,来寻求被害配偶得对相奸人请求精神上损害赔偿之根据。
l)亲属权说——陈计男教授认为通好系侵害夫妻之亲属权。惟第195条所规定之种种权利中,并无亲属权。然其参照日本学者之见解,谓:“日本学者对于与‘民法’第195条相同之日本民法第710条的解释,认为条文所列身体。自由、名誉之侵害,系例示人格权之重要者,并非对于非财产上之损害得请求赔偿者,以身体。自由、名誉受侵害者为限”;进而引述1956年德国联邦普通法院之见解,已开始认为其他人格权之侵害,亦得请求非财产上之损害赔偿;且更具体举出1958年2月14日之判决,对于肖像权人格权之侵害,认为可类推民法第847条(类似“民法”第195条)规定,请求金钱赔偿。最后针对“最高法院”之见解作如次之批评:“(“最高法院”之判决认为)通奸系以悻于善良风俗之方法,破坏他人共同生活之和平、安全及幸福,得依第184条第1项后段规定请求损害赔偿。但其得以请求非财产上损害赔偿之依据为何,则未说明。1966年3月28日民刑庭总会时,对此似曾加以讨论,但似又因碍于第18条第2项规定,未能对此作正面之说明,仅决议:仍维持1952年4月14日之决议,其处境与德国联邦普通法院在1956年代之情形相问,尚不敢超越传统之桎梏诚属可惜,实有待于法律解释权之进一步运用”。该文中并未明白指出第195条为例示之规定,而亲属权之受侵害可依该条规定请求精神上损害之赔偿。但从其引用日本学者之见解,德国法院判决之趋势及对于“最高法院”见解之评述,可以窥知其主张第195条规定为例示之规定,似无可疑。实务上,如 1969年台上字第 1347号判决(后述),即采同样之见解。
2)身份权说——孙森焱教授谓因通奸而夫妻间之权利若被侵害,被害人所致精神上之痛苦,当更甚于财产上损害,此项权利性质上属于身份权,似无疑义。依日本学者中川善之助博士之见,身份权与亲属权并无多大区别。但孙森众教授之身份权与陈计男教授之亲属机却有不同之处。亦即陈教授将亲属权视为人格权之一种,但孙教授认为身份权非人格权,既非人格权,即非当然可以适用第18条第2项之规定。
3)夫权说——史尚宽先生谓;“在民法上,应解释与妻相奸之第三人,对于夫之夫权或名誉权,同时加以侵害,虽非财产上之损害,亦应赔偿”。此说仅论及妻通奸时,侵害到夫之权利,而夫通奸时,是否侵害到妻之权利,则只字未提。至于夫权,如后述1952年台上字第278号判例之谓,“民法”亲属编施行前之所谓夫权已为现行法所不采,故与有夫之妇通奸者,除负刑事责任外,固无所谓侵害他人之夫权。此说与现行“民法”之精神不符,含有浓厚的封建色彩,显然违反男女平等之原则。
4)名誉权说——史尚定先生认为相好人侵害到夫权及夫之名誉权,已如前述。何孝元先生亦认为因配偶通奸所受侵害之权利为名誉权,其谓:“‘民法’第184条所谓损害,原则上以财产的损害为限”,因此,明知为有夫之扫而与之通奸,纵属第184条第1项后段所谓以悖于善良风俗之方法,加损害于他人者,亦不得径解为夫有慰抚金请求权。虽然,妻之贞操受侵害时,其夫之名誉,实因而受损,精神上即感受痛苦,夫之所以得请求非财产上之损害赔偿,并非由于夫权受有侵害,而系因其名誉权受侵害使然”。王泽鉴教授亦认为实务上被害配偶可依第184条第l项后段规定请求精神上之损害赔偿,实可谓“于法无据”。自方法论而言,应于现行法上得请求慰抚金之规定中寻求根据。基于此种方法论上之认识,其认为“婚姻关系具有人格利益,放干扰他人婚姻关系者,除侵害被害人之亲属机(或配偶权)外,尚侵害被害人之人格;被害人感到悲愤。羞辱、沮丧,受人非议耻笑,其情形严重,就现行法规定而言,与名誉遭受侵害最为接近,故在解释上,可认为系名誉权遭受侵害,被害人得依第195条第1项之规定,就非财产上损害,请求相当金额之赔偿”。此说于规定不完备的现行法上,对于有限之法规作了适当之解释与活用,将“干扰婚姻关系”之案例,纳入现行法律体系之内,于现行法规之中寻求根据,在法的安定性与法的具体妥当性之中求得妥协,充分发挥了法学方法论的最大作用。惟名誉权受侵害,有其一定之成立要件。在通奸事件上,依上述可知,须受人非议耻笑,且清形严重者,始构成名誉权之侵害。若不受人非议耻笑,则纵然被害人感到悲愤、羞辱、沮丧,亦纯粹其个人感情遭受打击,与其名誉无关。将被害配偶所受侵害之权利,解为名誉权,固无不可,只是被害配偶之慰抚金请求权之成立,须受某种条件之限制,此对于被害配偶之保护是否周到,尚有待检讨。且清形严重者,应如何判断,亦无一定之标准;又情形严重与否并非关系着请求赔偿金额之多寡,而是影响到赔偿请求权之有无,此亦为此说值得注意之点。
3.由以上所述可知,台湾地区关于被害配偶团通好所受侵害之权利,究属何种性质,众说纷坛。日本实务上关于被害配偶请求赔偿之根据,亦未见统一。但日本民法因无台湾地区第18条第2项之限制规定,因此,在解释上不会发生问题。依通说,日本民法第709条(相当于台湾地区第184条)之损害,不限于财产上之损害,即精神上之损害亦包括在内;而日本民法第710条(相当于台湾地区第195条)之规定,不是列举的,而是例示的、注意的规定。如此解释,则因通奸所发生之精神上的损害赔偿,即可随心所欲地适用日本民法第709条、第710条之规定。依统计,从昭和二十五年至昭和五十四年之间,有36个关于通奸之判决。其中
对个判决肯定了因通奸所生之精神上的损害赔偿请求权。而其所持之根据、理由,大约有五:(1)夫或妻之权利的侵害;(2)守贞要求权之侵害;(3)参与守贞义务之违反;(4)家庭和平之侵害;(5)名誉权或人格利益之侵害。而否定赔偿请求权之5个判决中,有4个案例是在婚姻关系发生破绽后,才有通奸之情形。其中有3个判决认为夫妻在婚姻破绽后,已失去要求对方守贞之权利,因此,其通好行为不具违法性(横滨地判昭和四十八年六月二十九日判例夕亻厶ス”299号336页,东京高判昭和五十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判例时报810号38页,东京高判昭和五十二年八月二十五日判例时报872号88页)。另有一案例,亦在婚姻破绽后才有通奸之情形,但该判决并不以守贞期待权之丧失为理由,而认为虽然被害配偶因通奸而受精神上之痛苦,但难以认定相奸人系以诈术。诡计等不正之方法诱惑通好配偶,因此,其通好行为尚不足构成侵权行为(鸟取地判昭和四十四年三月三十一日判例夕亻厶ス”235号240页)。但日本最高法院仍然坚持肯定说,认为与夫妻之一方配偶有肉体关系之第三人,只要有故意或过失,则无论是诱惑通奸配偶或因自然之爱情而至发生肉体关系,均侵害他方配偶之作为夫或妻之权利,其行为具有违法性,应赔偿被害配偶所受精神上之损害(最高裁昭和五十四年三月三十日民集33卷2号303页)。
关于相奸人之责任,日本学说上或实务上之采肯定说者,均以侵权责任论之。但关于通奸配偶之责任,则通说与实务上之多数见解不一致。亦即实务上认为通奸系相奸人与通奸配偶对于被害配偶之共同侵权行为,因此应负共同侵权责任(大判昭和二年五月十七日)。但通说则认为亲属义务者之义务违反为债务不履行,不构成侵权行为。如前所述,在下级审亦可找出采取债务不履行说之判决。站在婚姻契约观之立场,将婚姻契约义务之违反,视为债务不履行,乃当然之归结,况且于日本,债务不履行亦可请求精神上之损害赔偿。
第三节台湾地区实务上之见解
“最高法院”之判决。判例或民刑庭总会决议,关于因通奸所生之精神上的损害赔偿多采肯定说,上所持之理由并不一致。而关于所侵害之权利究属何性质,亦会举行3次民刑庭总会加以讨论,但毫无结论。判决。判例中,有的课以相奸人侵权行为责任,有的论及夫妻相互间之责任,兹俄上述之分类,将其分成两部分,录其要旨,分述如下:
一、相奸人之责任
1.1952年台上字第278号判决(判例):“民法”亲属编施行前之所谓夫权,已为现行法所不采,故与有夫之妇通好者,除应负刑事责任外,固无所谓侵害他人之夫权。惟社会一般观念,如明知为有夫之妇而与之通奸,不得谓非有以违背善良风俗之方法,加损害于他人之故意,倘其夫确因此受有财产上或非财产上之损害,依第184条第1项后段,自仍得请求赔偿。
此判决否定了夫权之存在,而肯定夫妻因结婚而有法律加以保护之利益,此种利益受到侵害而有财产上或非财产上之损害时,得依第184条第1项后段规定,请求赔偿。可知,此判决认为被害配偶因他方配偶通好所受侵害的,不是权利,而是法益。此亦为此判决与上述诸学说不同之点。
2.1952年4月14日民刑庭总会决议:乙与甲之妻通奸非侵害甲之名誉权,仅系第184条第1项后段所谓故意以悻于善良风俗之方法加损害于他人,甲因此与其妻离婚,如受损害,自得请求乙赔偿。
此决议认为相奸人并非侵害配偶之名誉权,从而被害配偶不能依第195条请求赔偿,但与前述判决同样认为得依第184条第1项后段规定请求。值得注意的是,其谓“甲因此与其妻离婚,如受有损害”,似在强调相好人之通奸行为致被害配偶与其妻离婚,而受有损害,即通好与损害之间尚须有离婚为桥梁,才有因果关系之存在。惟受有损害并不以离婚为要件,不离婚而受有损害时,似亦可依第184条第1项后段规定请求赔偿。此决议之“甲因此与其妻离婚”等语,似有画蛇添足之嫌。
3.1955年6月7日民刑庭总会决议:查本院1952年4月14日回刑庭决议录载“乙与甲之妻通奸,非侵害甲之名誉权”,同年上院第 278号判例载“与有夫之妇通奸者……固无所谓侵害他人之夫权……”两者均载在判例要旨续编,该决议案与判例并无抵触,妻与人通奸,并无损害夫之名誉权。
1952年台上字第278号判例所否定的是夫权,而1952年4月14日民刑庭总会决议所否定的是夫之名誉权,夫之名誉权与夫权在性质上并非相对践的,既然如此,决议与判例当无抵触之处。况且判例与决议皆认为通奸系以违背善良风俗之方法,加损害于人之行为,结论是一致的。由此决议可知,实务上不认与有夫之妇通奸系侵害夫权或夫之名誉权。
4.1963年台上字第3232号判决:夫妻关系虽甚密切,而人格则各别独立,妻与人通奸时,虽应受刑事之处分,但夫之名誉或自由固不能因此而认为被侵害,故夫因妻与人通奸,除具体之损害,得依第184条第1项后段请求赔偿(例如夫因此与妻离婚如受有损害,自得请求奸夫赔偿是)外,不得以侵害名誉或自由为由,遽行精求赔偿。
此判决认为离婚而受有损害为具体之损害,似谓如未离婚,则无所谓具体之损害。以离婚与否来决定损害之有无,与1952年4月14日民刑庭总会决议陷于同样之错误。此判决于名誉之外,又举出自由亦不因通奸而受侵害,此为前述判决或决议所末提及的。
5.1965年台上字第2883号判决:人之家室有不受侵害之自由,明知有夫之妇而与之通奸,虽不构成侵害夫之亲属权或名誉权,但是否侵害其自由权,非无审究之余地。
此判决之见解极为特殊,一反1963年台上字3232号判决之见解,认为夫之自由权可能因妻之通奸而被侵害。惟第195条所称之自由,主要是指身体行动之自由,人之家室有不受侵害之权利,固无可疑,但是否得以自由权解释之,则颇有疑问。此判决之受批评,乃可想而知。
6.1966年3月28日民刑庭总会决议:甲与乙之妻通奸,究系侵害夫之何种权利,乙能否请求精神慰抚金,本院1952年台上字第278号判例,于此情形,认夭对于所受非财产上之损害、亦得请求赔偿.但仅说明系适用第184条第1项后段,而未及“同注”第195条,1965年台上字2883号判决,认为人之家卓有不受侵害之自由,明知名夭立妇而与之通奸,虽不构成侵害主之亲属权或名誉权,但是否侵害其自由权,非无审究之余地。议决:仍维持本院以往1952年4月14日民刑庭会议议决案。
由此决议内容可以窥知,“最高法院”已意识到若欲承认被害配偶之慰抚金请求权,则必须在第184条与第195条之间.作一妥当之解释,可惜无法突破传统,以维持以往之决议为由,避而不论,含糊带过。
7.1969年台上字1347号判决:夫妻之关系,虽甚密切,但人格则各别独立。妻与人通奸、其夫个人之人格权或名誉.因不能因方法加害于人,且足以破坏其夫妻共同生活之圆满安全及幸福,使其精神上感受痛苦,第195条第1项所列被侵害之客体、系例示规定,此外夫妻共同生活之圆满安全及幸福,亦为应受法律保护法益之一。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妻通奸,实有侵害被上诉人夫妻生活之圆满安全及幸福,致其精神上受有痛苦,虽非财产上之损害,仍得请求上诉人赔偿相当之金额。
上述1966年3月28日民刑庭总会决议所未能解决的问题,终于在此判决得到解答。此判决反于以往实务上之见解,将第195条解为例示规定,扩大人格权之范围,魄力可住。且又具体指出,夫妻共同生活之圆满安全及幸福,应为受法律保护法益之一,为1952年台上字第278号判例作了补充的解释。尽管此判决之见解,在理论上令人有飞跃之感,但大胆地摆脱传统的桂指,在第184条与第195条之间作一合理的解释,其精神令人佩服。
8.1971年台上字第86号判决:原审虽以非财产上之损害,而得请求赔偿金钱者,依第195条之规定,以侵害身体、健康、名誉或自由之情形为限,被上诉人……固有相好行为,但对上诉人之身体。健康、自由,均无侵害可言,即就名誉论,依目前社会通常观念,夫与人通好者,其妻并不因此遭受歧视或讥笑,即其名誉并未受有任何损害云云,而认上诉人之请求非有理由,予以驳回,惟按侵权行为,系指违法以及不当加损害于他人之行为而言,至于侵害者系何权利,则非所问,又夫妻互贸诚实之义务,夫妻之任何一方与人通奸,其法律上之效果,均属相同,要不因社会观念不同而有差别。
此判决认为第二审以“就名誉论,依目前社会通常观念,夫与人通奸者,其妻并不因此遭受歧视或讥笑”等理由,而为不利于上诉人之判决,尚欠允洽,则似又反于以往实务上之见解,而肯定被害配偶之名誉权受侵害。
二、通好配偶之责任
l.1966年台上字第 2053号判决(判例):第184条第1项前段规定以“权利之侵害”为侵权行为要件之一,故有谓非侵害既存法律体系所明认之“权利”,不构成侵权行为,惟同条后段规定“故意以悖于善良风俗之方法加害于他人者亦同”,至于侵害系何权利,要非所问,而所谓违法以及不当不仅限于侵害法律明定之权利,即违反保护个人法益之法规,或广泛悻反规律社会生活之根本原理的公序良俗者亦同,通奸之足以破坏夫妻间之共同生活而非法之所许,此从公序良俗之观点可得断言,木问所侵害系何权利,对于配偶之他方,应构成共同侵权行为。婚姻系以夫妻之共同生活为其目的,配偶应互相协力,保持其共同生活之圆满安全及幸福,而夫妻互守诚实,系确保其共同生活之圆满安全及幸福之必要条件,故应解为配偶因婚姻契约而互负诚实之义务,配偶之一方行为不诚实,破坏共同生活之圆满安全及幸福者,即为违反因婚姻契约之义务,而侵害他方之权利。
前述诸判决皆是被害配偶请求相奸人赔偿之案例,而此判决是被害配偶请求命相奸人及通好配偶连带赔偿其精神上之损害的案例。此判决要旨之前段,肯定相奸人与通好配偶之共同侵权行为责任,认为通奸足以破坏夫妻间之共同生活,而非法之所许。而后段则强调婚姻契约之义务,故违反此义务则系侵害他方配偶之权利。似已认为婚姻关系对于夫妻能建立一种权利而受法律之保护,此点颇受王泽鉴教授之激赏,认为“理论上显有进步,立论亦甚精密”。惟既然通好系婚姻契约义务之违反,则似应含有债务不履行之性质。将此判例与日本之甲府地裁昭和二十五年十月二十五日之判决相对照,可发现用语上有雷同之处。推尽管用语或理由相同,但结论不一。亦即日本实务上,认为该判决系采债务不履行说,而台湾地区此判例,则适用侵权行为之规定。或许因为在台湾地区,债务不履行不能请求精神上之损害赔偿,因此不能不借用侵权行为之规定,使得被害配偶可以请求赔偿。不过至少由此判例之字里行间,隐约可以找出契约责任与侵权责任之请求权竞合的色彩,此亦可称为此判例之最大特色。
2.1967年台上字第95号判决:夫妻之一方与他人通奸,足以破坏夫妻间之共同生活,对于配偶之他方应构成侵权行为,至于有配偶之人通奸则属第184条第1项后段所谓以悻于善良风俗之方法加损害于人,为配偶之他方得请求加害人赔偿财产上或非财产上之损害。
此判决与前述1966年台上字第2053号判例系同一个案例。其明白指出,与有配偶之人通好系以体于善良风俗之方法加损害于人之行为,自应适用第184条第1项前段规定。至于通好配偶之责任,究应适用第184条第1项前段规定或后段规定,则未明示。若依上述判例认为系侵害他方配偶之权利,则应属第184条第1项前
段之权利侵害。如此解释,则相好人与通好配偶所侵害客体与责任之成立要件并不相同。亦即相奸人所侵害的是,被害配偶之法律所保护之利益,而通奸配偶则是侵害被害配偶之权利。既然所侵害之客体的性质有别,则侵害之成立要件亦随之有异。亦即相奸人须有故意为必要,而通奸配偶纵为过失亦为负责。
3.1971年台上字第498号判决,1974年台上字第520号判决之主要论点与1966年台上字第2053号判例大同小异,兹不赘叙。
总之,上述之判决、决议各具特色,有的认为第195条系例示规定,有的认为通奸会侵害配偶之自由权,但大多认为相奸人之通奸系以悖于善良风俗之方法加损害于他人之行为。既然适用第184条第1项后段之规定,则须以相好人有故意为必要,若不知对方为有配偶之人而与之通好,纵有过失,亦不负赔偿责任。由上述可知,这些判决认为第18条第2项之所谓特别规定,系包括第184条,而第184条之损害赔偿又包括精神上之损害赔偿,此由1971年台上字第498号判决中“依第184条第l项后段规定,仍得请求相当之慰抚金”等语,即可明知。惟1961年台上字第1114号判决认为“受精神上之损害者,法律皆有特别规定,如第18条、第19
条、第194条、第195条、第979条、第999条等是”,排除第184条于第18条第2项所谓特别规定之外。二者之见解互相矛盾。实务上为解决实际上之问题,实现具体之公平正义,往往会有政策上的考虑,以保护被害人之利益,但有时会因此而造成理论不一致的现象,而关于夫妻财产关系之种种判决,即为一明显例子。而
会造成此种现象之主要原因,是法规之不完备或木合理。此时,虽可以法解释之方法来填补法规之缺陷,但毕竟法解释方法不过为暂时的、过渡的方法而已,因此仍有待在立法上作根本的解决。
第四节 康德的婚姻理论与通奸当事人之责任
通奸是两个人合作始能完成之行为,因此,若配偶之一方因通奸而受有精神上之损害时,相奸人与通好配偶均应负赔偿责任。惟相奸人与通奸配偶之地位毕竟不同,因此关于其所负责任之性质,是否同一,不无检讨之余地。学说与判例采肯定说者,亦少有分别讨论相好人与通奸配偶关于损害赔偿责任之性质。欲究明相好人与通奸配偶之责任,则须知悉夫妻相互间之权利义务,而此又须先了解婚姻之本质。本文将以颇具近代化的康德婚姻理论为基础,逐步论及相奸人与通奸配偶之责任。
1.首先康德将婚姻下了定义,谓婚姻为男女双方以其性的特征为一生的交互占有。他把婚姻关系分为对人类之物的支配面及人格的支配面,而加以分析。夫妻相互以对方为物而加以占有,并以对方为人格而加以使用。由于婚姻之成立,夫妻互相拥有“对物的对人权”;所谓“对物的对人权”是对物权与对人权的统一形态。其所谓之“对物权”是得以对抗天下万人之绝对的、观念的权利,亦即近似于物权。其所谓之“对人权”是对于作为自由意思主体的法人格者的请求权,亦即近似于债权。详言之,其认为婚姻是男女双方互相以对方为物及人格的结合;而基于婚姻,互相对于他方拥有两种权利,一是对人权;一是对物权。而发生此两权利之基础是双方的自由意思,此贯彻者近代市民社会之“契约自由”之大原则。婚姻为人格主体间之契约,透过此契约,人格主体在性方面互相有权请求对方履行某作为或不作为义务,再透过此权利而对于他方之肉体加以占有、使用。夫妻之对人权,具有债权之性质,再具体言之,夫妻之对人权为请求对方提供肉体之权利。夫妻之对物权,具有物权之性质,亦即夫妻相互具有物权的支配关系。夫妻立于相互支配关系而拥有之权利,即是可以排除第三人之独占的、排他的配偶权。此贯彻着近代市民社会之“所有权不可侵”之大原则。
康德的婚姻理论,明白说明了近代一夫一美制的本质,同时将近代市民法的两大基本原则——契约自由与所有权不可侵——导人了婚姻关系,确实有其独到之见解。基于此见解,日本学者有谓一夫一妻制是近代婚姻本质的法的表现,与所有权之本质为同一基调。
2.基于康德之婚姻理论可知,夫妻相互拥有排他的、独占的配偶权,与有配偶之人通奸,就是侵害被害配偶之排他的、独占的、配偶权。判例强调通好系悻于善良风俗之行为,加上有加害之故意,而具有强烈之违法性,故认为被害配偶得依第184条第1项后段规定请求损害赔偿。此种见解,固无不可,但若能将通奸解为系侵害被害配偶之配偶权,或较能保护被害之配偶。如前所述,既是权利之侵害,则不必限于故意,即有过失,相奸人亦应负赔偿责任。此时,被害配偶请求相奸人赔偿损害所依据的,不是第184条第1项后段之规定,而是同条项前段之规定。如此解释,也更能符合近代一夫一妻制之本质,而且贯彻了市民社会所树立之所有权不可侵之大原则。
惟有问题的是,被害配偶可否请求精神上之损害赔偿。此又涉及第18条第2项、第184条、第195条第三者之关系。关于此点,通说之见解认为,第184条第1项之权利包括人格权,但仅止于财产上之损害始可请求,而第18条第2项之所谓特别规定包括第184条。一般而言,人格权之受侵害,所发生财产上之损害不多,若依通说,则对于精神上受到侵害之被害人而言,实有欠公平。为了保护被害人之利益,填补其所受之损害,应给予精神上之损害赔偿请求权。基于此,“最高法院”乃创设一基本原则,使被害配偶得依第184条第1项后段规定,对相奸人请求精神上之损害赔偿。从法条之文义观之,第184条之损害赔偿,既未明定为财产上之损害赔偿,则解为包括精神上之损害赔偿,似无木可。若依通说,第184条为第18条第2项之特别规定,则第184条更应包括精神上之损害赔偿。如此解释,则不仅第195条第1项后段为注意的规定,即同条项前段规定,亦不过为例示的、注意的规定而已。确实此在理论上,难免令人有突然飞跃之感,而且根本改变现行损害赔偿法之基本体制,在法学方法论上,极为不妥。但,今日“最高法院”乃基于现行‘损害赔偿法”本身之缺陷,以致无法保护被害人之权利,因此才以解释的方法来填补此缺陷,虽然在理论上,多少有勉强之处,但亦为不得已之事。况且,外国立法例已渐走向扩大人格权范围的趋势,在台湾地区立法论上亦有修正第18条第2项为概括规定之主张,鉴于此,配合将来立法趋势之发展而为解释,亦可符合时代之潮流。
3.夫妻因婚姻契约之成立,而负有种种之义务,而这些义务之履行构成婚姻契约之实质内容,如互负扶养义务、婚姻生活费用负担义务或同居义务,而违反这些义务将构成恶意遗弃而为离婚之原因(1932年上字第259号、1933年上字第92对号、1931年上字第1569号。1933年上字第636号、1940年上字第254号人从“纯
契约”之观点来看,违反了这些婚姻契约义务乃为“债务不履行”,而为“契约终止”之原因。依康德之理论,夫妻相互有请求对方提供肉体之权利,而对他方有排他的。独占的支配权。从夫妻之义务面来观之,夫妻因婚姻契约之成立,在性方面,有作为与不作为之义务。具体言之,作为义务为对于他方提供肉体之义务,若拒绝提供,则属债务不履行。不作为义务为夫妻双方之守贞义务,即不为
通奸行为之义务,此不作为义务亦为给付内容之一,若违反此义务而为通好行为,亦为债务不履行。但配偶之通好行为不仅为单纯之债务不履行,正如判例之所谓:“配偶之一方行为不诚实,破坏共同生活之圆满安全及幸福者,即为违反因婚姻契约之义务,而侵害他方之权利”。由此可知,配偶之一方违反婚姻契约义务时,不仅构成债务不履行,若同时侵害到他方配偶之权利或法益时,不妨成立侵权行为。惟依“最高法院”判例认为当事人间有契约关系之连系时,侵权行为即不能成立(193年上字第1311号、1971年台上字第1611号、1972年台上字第200号)。依此见解,配偶间有婚姻契约关系之存在,配偶之一方与配偶以外之人通奸时,纵然扰乱他方配偶精神之安定,破坏家庭生活之和平,具有相当之违法性,亦仅是婚姻契约义务之违反,而无侵权行为成立之余地。如此,在债务不履行不能请求精神上损害赔偿之情况下,出现不合理之现象。亦即本来被害配偶可依侵权行为规定,请求赔偿,如今,因侵权行为被视为债务不履行之特别形态,依特别法优先普通法之原则,排除侵权行为之适用,使得被害配偶无法请求损害赔偿,此对于受有精神上损害之被害配偶而言,似乎过于苛酷。1966年台上字第2053号判例,或许早已洞察此一不合理,故谓违反婚姻契约之义务,系侵害他方之权利。判例虽未论及债务不履行,实则因于现行法下,债务不履行不生精神上损害赔偿之故。由此判例之内容观之,表面上,无请求权竞合之情形,但实质上,已否定了“最高法院”认为当事人间有契约关系存在时,不成立侵权行为之见
解,承认债务不履行与侵权行为有请求权竟合之可能,而为1974年台上字第1988号判决立下了基础。
第五节 将来之课题
一、性道德的变化与通奸当事人之责任
由对妻单方面的要求守贞进化到夫妻互负守贞义务,是男女不平等迈向男女平等之一大进步。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性道德、性观念又有急激的变化,康德之排他的性爱观已渐不被采纳,取而代之的是不干涉相互之自由、抑制爱的嫉妒心之论调,似有返噗归真而走回未开化民族不重视贞操观念的时代。各国在立法或司法时,多少受到此观念之影响,对于夫妻之守贞义务亦不作严格之要求。日本刑法于战后,就将通奸罪删除,而下级审判决关于通奸之违法性,亦反于最高法院之见解,认为基于自然合意的通好行为,尚难谓为具有违法性(鸟取地判昭和四十四年三月三十日)。学者如加藤一郎、岛津一郎、上野雅和、沉井裕等亦采此说。美国1976年之后,实务上认为夫因妻之通奸而对相奸人请求损害赔偿,
乃是在道德、性、伦理面上的时代错误,有认为要已婚者因与他人有自然的、自发的性关系而负责任,已非国家所关心之事,甚至认为此种损害赔偿之请求,是侵害个人基于自然合意性关系的隐私权。英国于1970年修改正法,删除了因通奸所生之损害赔偿请求权。从这些外国判例、学说或立法之变化,可以窥知该国之性道德、性观念已有显著的变化。将通奸视为自然的爱情,而将通奸之问题委之于自然爱情之竞争来处理,此种观念,在现行法体制之下,恐怕尚难为学者或实务家所接受。但性道德、性观念之改变,将会影响相奸人责任之有无或轻重,此亦值得注意的。
二、婚姻关系破绽后,对于守贞义务之要求程度
婚姻关系发生破绽后,夫妻有名无实,此时,夫妻互相要求对方守贞之程度。已不如圆满、幸福生活时之强烈,甚或不在乎对方配偶之不贞行为。若仅存着仇恨心理,向相好人或通好配偶请求赔偿时,是否应否定其赔偿请求权?实务上在处理通奸之案例时,似应斟酌通奸时婚姻关系已否发生破绽,以决定请求权之有无,或请求金额之多寡。
三、子女利益之保护
有未成年子女之人,抛家弃子,与相奸人同居、通奸,则通奸配偶对其末成年子女未能尽到教养及保护之义务(第1084条第2项),使得该末成年子女遭受木利益或精神上的打击。该子女之遭受不利益或打击乃国通奸行为之所致,此时,能否向相好人请求损害赔偿?“最高法院”认为:“至于母将子弃置不顾,子因此所受精神上之痛苦,乃母子间天性关系,亦难谓被上诉人(相奸人)有何侵害行为,上诉人父子请求被上诉人赔偿慰抚金,即非正当”(1963年台上字第3232号),否定了子女之赔偿请求权。但日本下级审多肯定子女对相奸人有赔偿请求权。即认为近代的家族关系以一夫一妻制为原则,通常是由夫妻或其末成年之子女所构成;各构成员之精神的和平、幸福感及其他相互间的爱情利益,为法律所保护之人格利益,因此,侵害此种利益当然构成侵权行为。为了保护未成年子女之利益,是否应肯定其损害赔偿请求权,也是今后研究人格权之一大课题。
四、“民法”第18条第2项之修正
随着时代的进步,社会关系日趋复杂,人格权之范围日益发展扩大,立法上似应广泛承认被害人精神上损害之赔偿求权,此不仅无人格商品化之忧,反而尊重被害人之人格,唤起个人对人格之自觉及社会对个人人格之重视。况且,民事赔偿之目的,在于填补被害人之损害,若被害人人格受损,精神遭受打击,却囿于人格商品化之限制,而令被害人无法请求赔偿,则岂不本末倒置?今日,学说莫衷一是,判例见解不一,均因第18条第2项之规定不合理所致。台湾地区似应参考先进诸国之立法例,修正第18条第2项规定为概括规定,如此,既可免于众说纷纭之忧,又可符合时代潮流。新修正之“民法”总则,仍然保留第18条第2项规定,实属遗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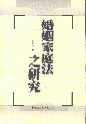 《婚姻家庭法之研究》:
《婚姻家庭法之研究》: